首页 > 正文
中国政法大学陈夏红: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深圳贡献”在于推出破产行政机构
2020-07-15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郑玮,周南
如何解读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重大意义与尚存的争议?
不久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就《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一直备受关注。作为我国拟出台的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个人破产条例在完善现行破产制度,健全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围绕个人破产条例的出台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旨在为债务人提供依法免责“避风港”的个人破产条例应如何平衡债务人的免责利益与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如何能够避免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恶意逃债”进而损害债权人的清偿利益?诉讼成本较高的破产重整制度是否适用于个人破产?设立依职权启动破产制度能否彻底打破“执行不能”僵局……
针对上述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
个人破产制度对债权人亦具有积极价值
南方财经:当前世界各国破产法的保障本位明显向债务人利益方向倾斜,个人破产条例应该如何平衡债务人的免责利益与债权人的清偿利益?
陈夏红:从理念层面,现代化的个人破产制度最为重视的价值之一,就是对债务人的宽恕和原谅。从人类破产制度文明进化的历史来看,破产制度中对待债务人的残酷性,整体来说,越来越低。从早期的生命抵债、人身抵债、劳役抵债,再到现在的即时免责制度,这是个人破产制度进化的成果,是现代化个人破产制度的底色。
这也是个人破产制度和企业破产制度最大的差异所在。企业破产程序特别强调对债务人企业的拯救,因为我们确信拯救会增进债务人、债权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但个人破产不尽如此,个人破产制度更讲究对债务人的解救,这种解救以宽恕和原谅作为基本底色,时间上越迅捷越好。
比如我们常说,个人破产制度能够保护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能够保障企业家精神,能够促使个体在创业开展必要和适度的冒险,进而促进社会创新。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机制,一旦创新失败,很多本来很具有企业家潜质的债务人就要踏上不归路,把个人、家庭、债权人和全社会都拖入债务的死结。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个人破产制度总是被认为更偏向债务人。但我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债权人的积极价值,也不应该忽视:第一,个人破产制度能够提高债权人的预期,也能够督促债权人在放贷前尽必要的审慎和审查义务,能够保障债权人的经营活动更为理性和稳定。第二,个人破产程序作为集体清偿程序,可以避免债权人为在执行竞赛中胜出而付出额外的成本,尤其是避免债务催收等灰色地带的违法成本,也能够避免一些社会悲剧。第三,破产程序清晰的清偿规则,能够极大地解决债权人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认知困境,也有助于债权人及时通过个别执行或者集体清偿,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南方财经:与公司运营相比,公民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更灵活多变,也因此导致个人破产制度更容易为个人所滥用。在政策制定层面,应如何避免个人破产制度被滥用?
陈夏红:任何制度只要涉及利益的调整,无论是哪方面的主体,就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尤其是制度设计不够精密,滥用的违法成本很低的情况下,滥用几乎不可避免。在这种认识前提下,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制度设计中尽可能周全考虑,多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个人破产制度的设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大胆学习。
另一方面,制度构建中,需要未雨绸缪考虑实施评估和修订问题;在制度落地后,需要加强实施状况的调研和及时评估,并将实施中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立法机构,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完善。尤其在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法律的及时修订和调整,可能比法律的稳定性更为重要。
就具体制度设计而言,我认为防止个人破产制度滥用,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程序设计应特别强调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加强债务人的披露义务,确保债务人披露的真实性。如果事后发现债务人披露或者申请材料造假,需要通过事后惩罚机制,让债务人付出远高于其所得的代价,进而也引导其他债务人诚信破产。
第二,在惩罚措施的体系化方面需要特别用心,既要让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能够通过个人破产程序解套,也要让试图通过个人破产逃废债的债务人,付出远高于其所得的代价,让其不敢滥用、不愿滥用、不能滥用。
第三,要利用技术手段,强化个人破产相关信息的追踪、互联和共享,无论是个人征信系统还是其他重大财产交易环节,都需要确保特定年限内的数据可检索、可共享,要通过技术化手段,确保对债务人的约束措施执行到位,而不是由债务人选择性执行。
第四,对于破产债务人的监督工作,应该由常设的破产行政机构承担并完成。现行《企业破产法》缺乏相关机制,但个人破产制度的运行特别需要这么一个机构。《深圳个人破产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有了探索和创新,希望能够尽快落地。
当然,防止滥用个人破产的举措,远不止上述四点。这一切措施的目标,都是为了让个人破产制度成为诚实人的游戏,而不是逃废债的天堂。
推出破产行政机构是深圳个人破产条例最大亮点
南方财经:此次深圳个人破产条例制定了3种个人破产程序,包括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但有观点认为,破产重整制度并不适用于个人破产,因破产重整制度的贯彻实施涉及技术、金融、社会协助等各个领域,程序复杂且耗费较大,个人破产重整的诉讼成本或将大于诉讼效益。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陈夏红:我认同这种看法。个人破产的本质,就是给债务人即时免责,让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通过个人破产程序,能够摆脱债务的泥潭。站在理性的角度,如果一边是立即的、彻底的免责,另一边是三五年后持续还债后的免责,尽管前者限制可能更多,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快刀斩乱麻解决麻烦,而不是将未来的三五年的收入都跟偿债计划绑在一起。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设计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的个人破产程序,我猜测一方面是为了最大限度跟《企业破产法》对接,减少分歧和争议,另一方面可能是起草者对于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价值的认知混淆,忽略了两种主体破产程序在价值追求方面的泾渭之别。
美国针对个人债务重整的第13章一直饱受诟病。其最初就是给有预期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债务人设计的,经过几十年演化,尽管还保留在立法中,但越来越受到债务人理性的抵制,越来越尴尬。
在实践中,债务人希望获得第7章的即时免责,重建生活,而不愿意选择第13章程序,把未来3-5年的收入拿出大部分用来还债。美国的立法者为了把债务人从第7章破产清算驱赶到第13章,不得不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胡萝卜”就是不可豁免债务和担保债务都有了协商空间,“大棒”就是通过收入测试,强制要求预期收入符合条件的债务人不得选择第7章。
这已经成为美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缺陷,美国破产协会2019年4月发布的报告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在构建个人破产制度时,应该多开眼看世界,尤其是尽可能避开其他国家和地区走过的弯路。
南方财经:目前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设计是以债务人或债权人申请为启动破产程序的前提条件,是否有必要考虑赋予法院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的权利,以彻底解决“执行不能”问题?
陈夏红: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审慎。破产程序是一种终局型集体清偿程序,也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对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在内当事各方的实体性权利,会有重要影响。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意思自治”,相信理性经济人的存在。
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部门利益、人为因素、制度缺陷等等因素,一定会诱使权力的过分行使。尤其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执行难”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果放开依据国家职权启动个人破产程序,那么个人破产程序可能会成为执行部门的“垃圾桶”,只要执行不了或者执行困难的案件,可能都会扔给破产庭去处理。
但是,执行部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破产庭有可能更解决不了。因此,国家公权力机关依据职权启动破产程序的想法,在当前应该十分慎重,否则很可能会在债务违约本身带来的困境之外,再给当事各方带来更大的困难。
无论如何,破产事务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中自生自发的部分。我国破产制度构建,一直是当事人申请启动模式,本质上是对公权力机构依据职权启动破产程序的自我约束。依托《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而落地的执行转破产制度,其实是打了个擦边球,从实务角度可能不得不然,但从学理角度还是有争议。如果鼓励国家公权力机构积极、主动介入破产事务,不仅会消解破产法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法的认知,也可能导致不必要地深度介入经济生活,反过来也会给公权力机构带来重担。
南方财经:个人破产立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顺利落地施行需要诸多法律制度的配套支持。若个人破产条例要在全国推行,需要构建和完善哪些配套制度?是否需要考虑建立专门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制度?
陈夏红:跟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制度相比,就个人破产制度运行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破产行政机构。至少就个人破产制度而言,破产行政机构有可能比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更关键。
我印象中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讨论过,个人破产程序本质上究竟是行政属性还是司法属性?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否认,个人破产程序中涉及大量行政层面的内容,比如债务人的监督,比如个人破产案件的管理,比如个人破产免责的决定等等。如果有合理的破产行政机构及职权分配,司法层面的压力会小很多。这种情况下,是否建立专门的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制度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推出破产行政机构,我认为这是《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个人破产制度和程度设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可能都会有差别,细节问题可以边实施边完善。但破产行政机构的设立,不仅对于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对于解决企业破产制度中的部分顽疾也十分重要。深圳在构建个人破产制度过程中推出破产行政机构,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中央层面,我认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也可能是真正的“深圳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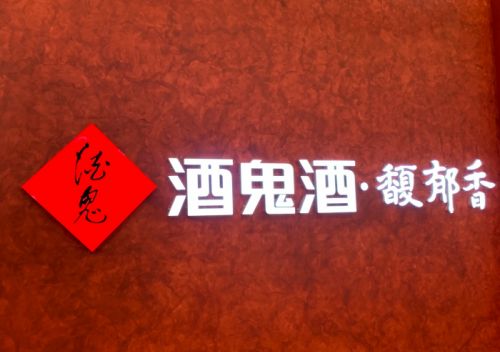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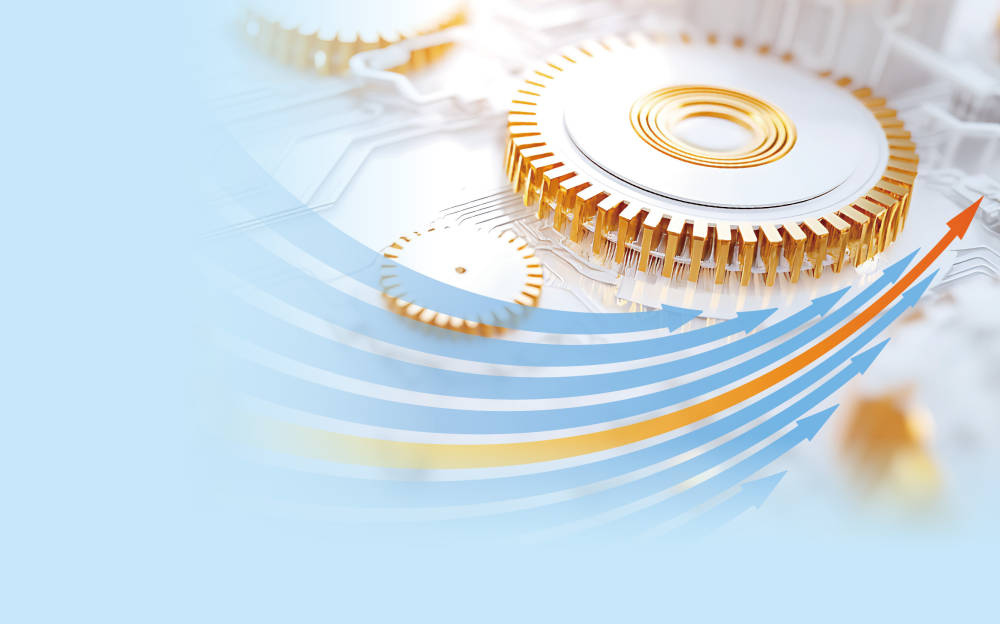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579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579号